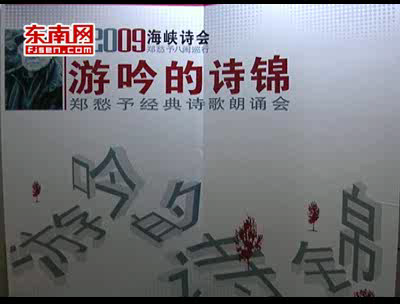一天,连顺舟正在读《阅微草堂笔记》,忽然家人来报,说有个外乡人求见,赖在门口不走,非要见连老爷不可。连顺舟问:"他有什么事?又是共产党的游兵散勇来避难讨口饭吃的?"家人笑道:"连老爷料事如神,来人还背着一杆火铳呢。"连顺舟将目光收回书卷,挥手道:"那还见我做什么?带去乡上就是了。"家人道:"他不肯呢,说非要面见连老爷。"连顺舟一怔。"怎么,他还要讨个官做?带他进来。"来人十八九岁,个子又矮又瘦,一身破衣烂衫,掩饰不住身上的几道伤口,污血在伤口处都结痂了,引来几只苍蝇嗡嗡打转。此人眉眼清秀,透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机灵劲,特别是那隐隐的倔劲,让连顺舟心中一动。
"小兄弟,你见我什么事?"连顺舟问。
"我要当红军。"来人一个字都不肯多说。
"当红军?怎么投到我这来了?"连顺舟一笑,扔掉手上的《阅微草堂笔记》。
"连老爷做过红军连长,肯定知道红军在哪。"
"我当然知道,红军都在山上呢,你可以去找啊。"
"闽西处处山,哪座山上有红军?"
连顺舟笑笑,停了片刻说:"小兄弟,听口音你也是上杭本县人。你看你,饿得连火铳都扛不动了,还要找红军呢,你先去吃顿饱饭,换件衣裳,再给伤口上点药,完了就回家吧。"
不料,来人"哇"地一声号啕大哭,边哭边说:"我没有家了,我家人都被白狗子杀光了……"
连顺舟皱皱眉,他不喜欢男人这种哭法,哭天抢地的,男人有泪,应当无声慢流,那才是蓄养着复仇的力量。
"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黄松。"
止住泪水的黄松说,他和父亲、哥哥都参加了村里的"铁血团"。暴动失败后,钟绍葵的民团带着白军杀回上杭,他父亲和哥哥还有弟妹都被他们杀死,全家人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他想通过连老爷指条道,找红军,为全家人报仇!连顺舟听完,疑惑地问:"白军是全村灭门,还是单杀你全家?"
"灭门的还有村苏维埃主席一家,龙岩来的谢先生,那是共产党派去的好大的官,也被白狗子在头顶浇上煤油,点了天灯……"
"你是村苏维埃的干部?"
"不是……我、我参加了村上铁血团,还动手砍过村上财主的脑壳,我本来不愿意动手,他还是我的东家,苏维埃和谢先生非让我砍,我就砍了……"黄松怯生生的。
连顺舟冷笑一声。"难怪呢,人家会专找你全家灭门。冤有头,债有主啊,等共产党红军回来了,你再杀尽土豪劣绅,报仇雪恨,冤冤相报。"
连顺舟最听不得杀人,特别是杀有钱人,所谓土豪劣绅。你共产党打土豪的目的不就是分田分地分浮财嘛,东西拿去就是了,动不动杀人就不好了。就连动物之间争食,还不至于相互残杀呢。人可是万物之灵啊。他不满的目光,落在了黄松肩上的火铳上。"黄松,你这鸟枪还打得响吗?"
"指望它报仇呢。"
连顺舟推开房门,站在土楼的环形走廊上,他抬头望,不见飞鸟踪迹;低看头,圆形的土楼天井中也没见一只老鼠。只有一只花狗翘翻了肚皮,懒洋洋地晒太阳。
他回头招呼道:"黄松你来,那只花狗打得中不?"
黄松愣住了。就是跑得风一样快的山麂,他都有把握一枪撂翻,他不晓得连顺舟搞得什么名堂。
"开枪吧,打得中你留下来……不是说狗,我是说你可以在我这留下来,日后我保证送你去找红军。"见黄松仍在发愣,他又说:"先收收心吧,闽西地面刀光血影的,人家到处追剿暴动的铁血团,除了我这,你还能去哪?"
"连老爷,我不是那意思,我是问,这谁家的狗?"
"还能有谁家的?我家的狗。"连顺舟淡淡道。
黄松二话没说,麻利地摘下肩头的火铳,直指天井,没等连顺舟反应过来,"轰"的一声巨响,似乎震得整座土楼都打了一下晃,一股子蓝色火硝子味刺鼻地呛开来。天井中那只花狗一声惨叫,像被人捉住四腿高高抛起,弹到了空中,狠狠地跌回地面时,一动不动了。连顺舟探头看,花狗的脑袋几乎被打碎了。枪声引发了土楼内的惊慌,女人哭、男人叫,那二十多名快枪手纷纷提枪冲出,却不知目标何在,最后围着一只死狗四处张望,待看到楼上走廊的连老爷正笑眯眯地发笑,仍然不知发生了什么。连顺舟摆摆手说:"没事了,都散了吧,把那狗拖出去埋掉。"
黄松留在了连顺舟身边,成了一名快枪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