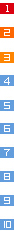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散文]克拉克瓷
| 2014-06-26 05:23:28 来源:百花文艺网 责任编辑:陈颖 我来说两句 |
分享到:
|
1 在平和县克拉克瓷展览馆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破碎与残缺。在这间不足150平米的展厅里,那么多碎瓷被慎重地搁在红丝绒上,罩在玻璃罩里,即使摆放在玻璃橱里的那些较完整的瓷碗磁盘,也只是相对的完整,或多或少有着不同程度的损毁。这是我见过的最尊贵的破碎与残缺。这些瓷,它们曾经是有用的,我仿佛看见它们400多年前的完整,它们原本或是农家饭桌上一只简陋的碗,一只卑贱的碟,亦或是达官贵人厅几上贵重的酒觞、茶钵,这些蓝色花纹的器皿,或贵或贱,本都是日常的。然而,破碎是它们共同的命运,破碎使它们在当初使用它们的人眼里一钱不值了,它们被弃旮旯、荒野,然而,在时间的洪荒里,终于遇了那月光、那潮汐、那艏船、那些个人,使得那些瓷洗去百年尘垢,由日常转为艺术。一个俗物没了日常的用处,没了烟火味,反而变得更珍贵了,有了鼎鼎之美名——克拉克瓷,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接受人们膜拜的目光。 破碎里一定有故事,一本书里描写一个小女孩打碎了一个村妇的瓷盘,那瓷盘上画着很美的图案,写着天堂二字。那村妇痛哭,她心爱的瓷盘破碎了、她的天堂破碎了。小女孩被罚跪,从此开始了她破碎的一生。“破碎”有着吞噬一切的魔力,我也是害怕“破碎”的。虽说,我小时候从未因打碎什么被责骂,但那一声脆生生的响,带给一个孩子的惊恐是大的。长大后,按说自己有了经济实力,只要打碎的器皿不贵重也无妨。可是,那“破碎”一直在民间象征不吉的预兆,这样的暗示可以让人一整天忐忑不安。所以,在那破碎之后,人都反复念叨着:“碎碎平安!,取“岁岁平安!”的谐音,来安慰受惊的灵魂。如今,克拉克瓷破碎的故事早已灰飞烟灭,新的故事重新开始。 2 克拉克瓷大多是青花瓷,这被层层包裹的甘蓝,朴素又典雅,被它们照亮的一瞬间,世界便黯然了。我不能明白,所有我见过的“青花瓷”明明都是蓝色的,却用着“青”字来命名,以至于我不得不信,为此命名的人一定是个诗人,“青”这个字所营造的神秘、圣洁、诗意是无以伦比的。乍一看,克拉克瓷与别的青花瓷没有什么区别。细看,它的蓝拙朴些、滞重些。仿佛是用了满世界的蓝,反复用锤子敲打,一层一层嵌进瓷的身体里的。我以为那不是天空的蓝、不是海水的蓝,它没有那种辽阔与高远,它的蓝是农家主妇穿的丹阴士布褂的蓝。是日常的,可以抚摸的。 展览馆里所能见到较完整的青花图案,也许是受开光分格的局限,整个图案看去大多是规整的,拘谨的,很现实的那种,不敢有太多的想象与旁溢,盘、碗多是宽边的,沿口处多有圆形开光(开光,即在既定轮廓线条内进行的彩绘,有圆形、椭圆形、梯形、树叶形等),绘着山水人兽、渔樵耕读,构图严谨有序。虽是碎瓷,依然能看出克拉克瓷图案特有的粗狂与简洁,那些鸟兽虫鱼都有着安宁祥和的神情,那些梅兰竹菊都有着蓬勃之势,都很醒眼,留白处较少,略显繁杂,暗合了大众的审美与精神的需要。 听馆内工作人员介绍,克拉克瓷的风格与景德镇瓷相近,毕竟江西人在这里做过瓷。据载,明朝都察御史王阳明奉旨平乱后,便在此地设县,地名“平和”便是取“寇平而民和”的寓意。王阳明还从军中拣选了一些江西籍兵丁,充役于县治衙门等职。不仅首任县令是江西人,据考证,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江西籍人主政平和,使得景德镇烧瓷工艺传入平和。平和旧县城的九峰镇至今留存的“江西坟”,印证了那段历史。坟岗不远处便是克拉克瓷古窑遗址。 克拉克瓷不如景德镇瓷那般的精致细腻,其青花彩绘不重细节,施釉点彩较粗犷,随心所欲,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独具一格。倒也很受欧洲王公贵族的喜爱。克拉克瓷分万历至清初和康熙两个时期,前者有翠蓝、灰蓝、淡蓝几种色调,为开光的青花瓷,勾、点、染自然洒脱,凡圆圈皆两笔拼凑而成。后者胎薄。克拉克瓷与景德镇瓷最显著的区别是圈足的地方带着许多夹砂,即所谓的“沙足底”。《漳州府志》记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 不胜工巧的粗粝与拙朴更带了人间烟火味,在靠墙的展橱上,相对完整的两块大瓷,显然是昔日的大瓷盘,大瓷盘本就是农人灶台上盛红薯、米粥、盐咸菜的家什,是温老暖贫、日子笃实的象征。其中一个画着一只兽,好像是鹿;另一个画着一只飞起来的鸟,它那张开的翅子比所有的飞翔更持久,它一定是向着昨天的方向飞,昨天的昨天,它引领着我们这些凡人的肉眼,跟着它一起穿越、穿越,直抵洪荒、永远,那“永远”也只是承载我们目光的虚空。 3 从克拉克瓷展馆出来,我们去了克拉克瓷古窖址,“克拉克”这个洋名与“古窖”两个字的沧桑感怎么也贴合不起来,这样的对持倒更令人想到它的传奇与神秘。央视播出过《复活的克拉克瓷》与《寻找克拉克瓷的故乡》的节目,可我没有看到,我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它的身世,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了一艘“克拉克”号葡萄牙商船,船上近10万件中国青花瓷器因不明产地而被命名为“克拉克瓷”。 1984年阿姆斯特丹举办了题为“晚到了400多年的中国瓷器”的大型拍卖会,轰动了整个欧洲,全是打捞出的六七世纪沉船中的克拉克瓷,拍出了约3亿荷兰盾的天价。还有后来石破天惊的发现,平和窑遗址群解开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克拉克瓷产地之谜。据说一个为这项研究苦苦困扰多年的日本学者,当他来到这谜底—古窑遗址,竟激动地跪下来痛哭着。日本人真奇怪,懂得敬重神奇的物品,却不懂得敬重制造了这神奇物品的中国人。 汽车驶入平和五寨乡后,山路越来越崎岖,车子先是爆了一次胎,又在狭小的山路里被大石头卡住了,我与几个文友只得徒步行走。虽已深秋,路旁的山坡地、灌木丛依然飞红摇绿,空气清新可爽肌涤骨。远山全是规整的树木,那是农人栽种的柚子树,这人工斧凿的整齐划一很像某导演的方阵模式艺术,一种声势浩大的呆板,见不出灵气,却能让人深感人类创造力的巨大。 沿着有些风化了的石阶而上,石阶上覆着些细长的枯草,走在上面像是走在旧时光里。攀上 “狗头山”的山峦,终于亲睹这所谓的古窑遗址,只剩残垣断墙了,上面留下酱紫色的火烧痕有的呈瘤状突起,如同血痕,被称为窑汗。虽是这番景象,也不觉凄清呀落寞呀,其实这里已是一片柚园了,柚树蔽天遮日,有些树已收了果,像乳房干瘪的弃妇;更多的还挂着果,黄灿灿的,好不热闹。看得出农人的种植及一切活动避开了这古窑遗址,一种有意的保护,但却无法避开那些碎瓷片,其实那些柚树就生长在碎瓷与碎瓷的间隙里,在这里行走,一不小心就踩上了历史的碎片。 山下有一小溪迤逦而去,消失在崇山莽林间。文友H说,几百年前克拉克瓷就是沿这条溪流归棹远去,过漳州、进月港,一路奔流到海外。H还说当年文学大师林语堂也是沿这条溪流走向世界的。我遥想林语堂当年坐着乌篷船沿花山溪一路顺风顺水而去,很有些诗意的。这真是一条水上的丝绸之路,无论是瓷还是人,从这里流向世界,就不再被世界遗忘。 我们下到溪水里,濯洗捡来的瓷片,被泥土包裹着的瓷片。岁月的泥垢在清澈的溪水中褪去,精美的青花纹便显现出来,我手里的几块碎瓷有的像树叶,有的像繁体字,却看不出什么字,更多的是什么也看不出的花纹,由于破碎,图案被截断,便显出诡异与抽象。不需要看出它们的本相吧,这样美丽的花纹足矣。它们互相碰撞,发出了铿锵的金属声,是那样的悦耳。 4 从狗头山到碧沟窑,我们又看了几处古窑遗址,这所谓的“十里长窑”不免让我有些失望。秋阳下,只见蒿草在风中高高低低地摇晃着,有几处不明显的小土丘似的古窑遗址,没有我想象中的壮阔。如果当年没有葡萄牙“克拉克”号商船,没有被打捞出的六七世纪的沉船,那么谁还会来看这些藏匿在闽南大山里被抛荒的土丘?到处是那些半人高的野菊,它们硕大、金黄的花冠开得极灿烂,它们已经在这里灿烂过几百个秋天了吧?此刻,我所见到的野菊是否就是400年前开放的野菊?谁知这里发生过多少故事呢?看着那些窑汗,血痕一般的窑汗,还有那如荒冢一般的古窖,我忽然忧伤起来,我的忧伤像对面山岚飘忽的云雾,连我自己也看不清。古窖和墓地都是一种覆盖,像魔术家的手,在墓地隐秘的内部,肉体变成了泥土;在古窖隐秘的内部,泥土变成了瓷。宝石一样晶莹的瓷发生了怎样的质变?在此之前一定是一点一点的量变,然后才是质变。我从没见过任何质变的一霎那,我相信质变是一霎那的,缓慢的只是量变。神秘的大自然将它的奥秘向我隐藏,就像我从来不知道胎儿怎样在子宫里长出骨头。我不能知晓的东西总是比我知晓的东西多得多,无论我怎样努力亦是枉然。 5 我们去的最后一站是克拉克瓷研究基地,基地坐落在平和文峰的山窠间,翠岭青林环绕的一方空地,一个大的院子里,设有成品陈列厅,有窑房、水车、水锤、水床、淘洗池,还有手工制瓷流水线上的各道工序作坊。成品陈列柜里摆放着仿制而成的克拉克瓷器,有碟、盘、碗、罐、钵、瓶、杯、盏及笔架、墨架等。 一、二、三、四、五、六……我数不过来了,这些旧时光的翻版,这么多瓷瓶和磁盘,安静地排列在一大排瓷器架上。它们已经不带有任何泥土的表情,它们是脱胎换骨了的泥土。我常想这些明亮如玉的瓷,它们的前身竟然是泥土,这简直就是奇迹到荒谬的事情。我一直以为荒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真相。假如从没有人告诉过我瓷的由来,我能否知道它们来自于泥土,经水火而成呢?我想我断不能知晓这样奇妙的事。难怪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瓷,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一种宝石呢。我常想,第一个把泥土变成瓷的人是怎样的大天才呀!虽然他没有留下名字,像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没有留下他勇士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china,想起瓷,中国人该多么自豪呀。 院子里堆砌着做瓷的泥土,灰白色的泥土。听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是些特殊的泥土,叫“高岭土”。它们先是像被选秀的美女,在大山山脉里被海选了来,经过千锤百炼(30个小时的水锤击打),再经过四个水池的淘洗,留下细腻的过渡到水床,再经发酵,再经打磨,就成了柔软光滑细腻如缎的胚泥了。我一边听基地负责人介绍,一边把手伸进水床,感触着它们的细腻,尽管我和它们零距离接触,却不能深入泥土与水结合的隐秘之处。 6 这些泥土在艺工们的手里被铸造成各种瓷器,再放进窑里烧制而成。这些泥土有的被做成了鼎,象征着权力。我看到一个硕大的鼎被高高地摆在架子的最上面,基地负责人说是为一位尊贵的客人准备的。有的被制成盘碗瓶盏、文房四宝,小心地放在柜橱里,还有一些被制成坛子、钵罐,随便地贱放在地上。同去的一文友就买了一个回去腌咸菜。我想,同样的泥土,却有着贵贱不同的结局,瓷器也是有命的。这让我想到,在冥冥之中,是否也有一位造我们人类命运的神?造出一些尊贵的人,再造出一些卑贱的人。不公平就是另一种的公平,难道一个匠人没有权利将一些泥铸成鼎,将另一些泥铸成菜坛子吗? 同样是泥,却同途殊归,一些在制作过程中被摒弃了,一些要返工几次,反复几次回到初始,有的一次成型,有的经火后成为次品,是无法返工的次品,连重新来过的机会也没有了,它们的命运只能被丢弃。更多的是从泥土变为瓷,无法返回泥土了;作为人,我们却相反地走着回归到泥土的路,“你来自泥土,又回到泥土”。衰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退回到泥土的过程,我们其实说不清,我们每往前迈出一步,是前进还是后退。 在手工作坊,我看见泥胚在匠人的手里旋转着,那叫立胚,像地球一圈圈不停地转去,我们不也像这些工匠吗,每一天都是在旋转中度过的。这间作坊只有一对中年男女。他,那双手就是泥土延伸的一部分生命。我问了一句什么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跟他说话,他连头也不抬,他不理睬我。他纹丝不动,只有手里的泥胚旋转着。他灰头土脸,头上、身上到处泥痕斑斑,他整个人就是一泥胚。而我,衣着干净时尚地站在他面前。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在一个不搭理我的,一个灰头土脸的人面前自卑起来了,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卑与自尊是何等近的距离。也许他是对的,他为什么一定要理我呢?要对我客气呢?他知道我们不是冲着他来的,是冲着他手里的被造物。那些只认得物,不认得造物主的人,把造物主简单称为“打工仔”,让他们比所造之物更不如的家伙难道值得他们热情吗?他那双与泥胚同为一体的手,那双化卑贱的泥土为神奇之物的手似乎已超越肉体之身的手,他有权利睥睨我光鲜的衣裳与会朽坏的肉身。他的沉默是泥土的沉默,那是一种纯然的自我状态,永恒的宁静。是对外界的、可消逝事物的冷漠。也许这都是我的臆想,而他只是符合了《文心雕龙.神思》里说的那样,“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此时的他正摈弃一切杂念,进入瓷的境界。旁边那个和他一样灰头土脸的女人,见他不理我,似乎有些不忍,就跟我说起话来,可我一句也没听懂,不知道哪里的方言。让我更加尴尬。 另一作坊,艺师们正在施釉、绘画、加彩,所绘图案大多为民间喜爱的牡丹、荷花、竹子、松柏、鸳鸯、龙凤、麒麟等。一位正在给青花大瓷盘上釉的的艺师,同样是安静的,瓷一般的安静。我看着这青花克拉克瓷的蓝,忽然悟出,这蓝釉不都是丹阴士布褂的蓝,还染了一点点这山野葱郁的青,于是,它们成了最有生命力的颜色。 我感觉有些累了,就离开还在作坊里观赏的、兴致未尽的文友们,独自来坐在这院里的石蹲上,几声寥寥的鸟声,还有风声,这山野里的鸟声、风声似乎是瓷的同谋,让这空间越发得寂静,让我感觉时间凝固,白日冗长。 抬头,只见对面山上有一荒冢,我心里一凛,像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启示。我不知道那里埋葬着什么人,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已经归回泥土的人,回到了原点。其实,无论什么都会变成泥土的,据说人体的成分和泥土的成分大多一样,人的骨头由磷酸钙组成,磷酸钙就是泥土中成分之一。 7 我的记忆很差,也许和我多次手术,麻药的侵袭有关,也许和年纪有关。我们返回的时候,车子只拐了一个弯,那个刚刚自我介绍过的基地负责人,我已记不得了,名姓都忘了,甚至他的模样也是模糊的。当然,口袋里还装着他的名片,我的袋子里有很多这样的名片,这样陌生的名片。唯有那一幕,那泥土中的一男一女,做瓷的一男一女,在我心中永恒,麻药也不能抹杀的。我想,当年也一定是这样一些卑微的人,一些下里巴人,他们造的瓷已经名扬天下了,还被冠之“克拉克”的洋名。当然,我并不崇洋媚外。在瓷的面前,你无法崇洋媚外。 |
相关阅读:
 |
 |
 |
打印 | 收藏 | 发给好友 【字号 大 中 小】 |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证号:1310572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闽)字第085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网出证(闽)字第018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闽B2-20100029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闽)-经营性-2015-0001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东南网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职业道德监督、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591-87095403(工作日9:00-12:00、15:00-18:00) 举报邮箱:jubao@fjsen.com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