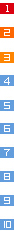我家乡是闽南小有名气的古镇(今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但八字缺“水”。方圆几十里地,不见溪流河汊,耳目所接,无非是褐色的土地。要说桥吆,唯有西边一座不到二三米长的石拱桥,叫着“翁墓桥”。据说本是没有桥,旁边原是一道坝,蓄水成潭。潭边有棵大榕树,虬干盘根,翠盖斜堰,密匝匝浓荫覆盖水面。晨曦夕照,姑娘媳妇手挽竹篮,三三两两结伴在此浣衣,潭面荡漾欢声笑语。
相传明朝正德年间,坐馆井头村的寒儒林希元偕妻携带一吊钱要去给岳父祝寿。行路至此,满头大汗,俯身擦擦脸,不小心那吊钱滑落到潭底。嫌贫爱富的岳父见他空手而来,便奚落他一顿。林希元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立誓出头之日,定炸大坝泻出潭水,让世人瞧瞧沉在潭底的那吊钱。后来,林希元累官至南京大理寺丞,炸了大坝。这一炸,恨是解了,路基却被冲垮了,塌陷成一道渠。乡亲们到邻近塘厝港搭船过海,要趟水过岸。后来不知谁建了家乡唯有的这座桥。
这小桥流水离小学不远,是孩童们的好去处。小时候,我们常三五成群到桥边玩。几株疏木,落日余辉漏下斑斑点点的光圈。桥下潺潺流水,冲击憨态可掬的卵石,溅起朵朵浪花。我们时而绕到树丛捉迷藏,时而到桥下拾卵石。风景这边独好,美术老师曾带我们到此写生。
家乡缺水,但先民们却以结满老茧的手,在田野挖了一个又一个的池塘,在田头掘了一口又一口的水井。池塘水井星罗棋布,滋润这方贫瘠的田垄。
家乡的池塘,要数翁墓桥右侧的“龙蛟池”最大。据说先前占地十几亩,端午节可在塘里赛龙舟。关于“龙蛟池”可有一段凄美的传说——
相传康熙、乾隆年间,宰相李光地的从弟李光墺之女要下嫁当地富绅林百万之子林中桂。为讨得李小姐欢心,林百万大兴土木,盖梳妆楼,楼前挖了个绿波浩渺的大池塘,楼后种了大片花圃果园,恢恢气势,人称“前渔池,后果园”。然这段婚姻却是“移桃接李”。李小姐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善弹琴,工吟咏,但所适的却是一个目不识丁、且痴又呆的。婚后不到三年,李小姐便忧郁身亡,玉焚香散。死前她借菊伤怀:“错下瑶池觅旧缘,埋沉幽谷自萧然。移根九畹香谁惜?纫佩三秋意共怜。瘦影凄凉悲露湿,残妆零落伴霜眠。冰枝羞染黄泥污,枉抱芳心度岁年”。
曾几何时,烟云过眼,脂粉荡涤,伊人何处觅?梳妆楼以自己独特的形象伫立在风雨之中,早已与现代的世界隔了几百年了。楼前那十多亩的龙蛟池也被周围的良田噬成一方小池塘,楼后的花圃早已荡然无存了,只有池塘旁的老榕树下留下些许残砖碎瓦。据说这里原有一座妈祖庙,香火很旺。后来遭日寇飞机轰炸,夷为平地。这断垣残壁也蕴匿了家乡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一旦人们要破译它,老榕树不见了,废墟上早已建起幢幢高楼。
这些零星的传说,已使我约略触摸到家乡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按沿海风俗,渡口码头往往有妈祖庙,供奉圣母娘娘。渔村的弄潮儿,他们扬帆出海,捕鱼为生,总是祈望海上保护神庇佑他们一帆风顺,岁岁平安。于是,建庙宇,祀奉妈祖。龙蛟池旁的妈祖庙,虽已成为废墟,但目睹这一切,我似乎感受到家乡的沧桑之变,很早很早以前,龙蛟池也许是个船坞,五月端阳才能在此龙舟竟渡。老一辈的乡亲常说,渔船顺着龙蛟池便直通到塘厝港。这只不过是一种揣测,我一点也不敢轻易下断论。但有一点不争的事实,家乡缺水,打出的井水,十有八九是咸水。而翁墓桥邻近的一片义冢地里,有棵乌甜树。树下有口井,天再旱,清冽甘甜的泉水便从泉眼汩汩流出,酒楼茶肆专门雇人到这里挑水,做出的汤鲜美可口,沏出的茶甘美醇香。
悠悠岁月,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亲浇灌农田,从井里打水、塘里汲水用的是乌杆、戽桶和水车。乌杆,这是杠杆原理的最简单运用。井边竖立长木柱作吊杆,木柱上横绑着一根粗的短木棍,与吊杆构成丁字形的。短木棍的外端捆绑一块石头,内侧垂吊几条绳索,是用来拉乌杆的。短木棍靠井的这一端,垂直吊着一根粗竹竿,竹竿的末端绑着一只矮墙的小木桶,作为盛井水用的。平时打水,只要一人扶着竹杆将桶按压到井里打水,另一端因绑着石头便下沉,随着石头的下沉,另一端的矮墙木桶就盛满水被提吊起来。旱时井深,至少要有二人,一人压桶,一人拉绳。“欸乃” 一声,水桶便吊上来,把水倒进田沟里,慢慢地浇灌庄稼。
靠近池塘边的田要灌水,就不是用乌杆提水,用的是戽桶或水车。水车昂贵,有的农户买不起水车,用的就是戽桶。戽桶是矮木墙箍就的,斜面,好进水,两边系上绳子。扯动着两边的绳子,戽桶就像蜻蜓点水似的,将水戽上田头,顺着畦沟流到田里。有时人手紧张,也有单人戽水的。戽桶一端的绳子拴在木桩上,另一端就单凭一人的腕力把水戽上来。别小看戽水,看似简单,双边动作若不协调,戽桶就不会吃水,便掠过水面,腾空而起,连半点水也戽不上。殷实人家备有水车。家乡的水车不是那种载一轮大得有点夸张的圆形风盘,凭着风力,悠缓地“吱呀”转动,斯泉涓涓……家乡的水车是龙骨水车,木质的,像长龙一样。车头安上两个大的木齿轮,车身有一大串的木片子。用时,把水车扛到池塘边,水车尾部浸在池塘里,临时车头搭一凉棚遮阳,棚里有扶杆。乡亲登上轮把,扶着扶杆,双脚踏轮把,齿轮一转动,片片木叶便把池塘水仄进车身,从车头吐出来,似蛟龙喷水,沿着水沟流到田里,滋润着作物。有时,乡亲们伏在扶杆上,口哼小曲,脚踩轮把,悠然自得车水,好一派农家乐。若遇到久旱不雨,池塘龟裂,井底干涸,庄稼快被烧焦。乡亲们心急如燎,眼里都快熬出血。为了争得一点水源,兄弟反目,邻里成仇,他们捏紧锄头、扁担,大打出手。家乡的械斗,逼得有的背井离乡,逃生异国他乡。他们告别祖宗,走过翁墓桥,从塘厝港乘船到厦门,被当着“猪仔”贩到南洋做苦力。人走多了,便成了侨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水田很少,多半是旱地。插不了秧,就种地瓜、大麦、高粱和花生。家乡人是“地瓜肚”,难得吃一顿饭。平时喝得是地瓜稀糊,这种稀糊是将地瓜磨碎,冲水过滤,上面的地瓜渣熬成稀糊,下面的地瓜水沉淀出白色的粉末,晒干就是地瓜粉,舍不得吃,拿到市场上卖。我还记得,妈妈为了让孩子吃上饭,有时用鸡蛋壳装米或缝了一个小布袋装米,放进地瓜糊里煮。熟了,剥开鸡蛋壳就是一粒鸡蛋饭,喷香又耐嚼。这是小时候一种特殊的享受。家乡还有一种“番洗糜”——“高粱稀粥”,以“土鬼脍”佐餐。高粱一粒粒像颗颗红珍珠,“土鬼”状如凤眼,腌熟了,拌上蒜绒,十分可口。传说有个落难皇帝逃到乡下,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乡人把中午吃剩的“番洗糜”和“土鬼脍”端给他吃。他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一扫而空,舌头还舔舔嘴唇,觉得比山珍海味还好吃。他便问这是何食物,乡人随口说:“珍珠糜凤眼脍”。后来,皇帝又重登皇位,回到皇宫,珍馐佳肴吃腻了,又想起乡下的美餐。待乡下亲手烹调的“番洗糜”奉到面前,皇上稍一沾唇,酸涩难咽,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地瓜糊,家乡人过去早就吃怕了。但现在有些老番客回唐山寻根问祖,要喝家乡水,要吃家乡饭。亲人特地煮地瓜糊款待他们。金灿灿的糊面浮着红心薯块,既香甜又爽口,番客吃得津津有味。
据说家乡的地形像一艘船,两头翘中间低,最低处是翁墓桥一带。1958年汀溪建起水库,为引汀溪水灌田,在翁墓桥一带架设一道悬空的渡桥,先是木质,后改为条石砌成的。渡桥在上,翁墓桥在下。渡桥似飞龙腾空,翁墓桥如小虫伏地,相形见绌。
家乡再也不缺水了。当月上梢头,晚风习习,我漫步在干渠的林荫道上,俯身掬了一口清洌甘甜的渠水。此时,远处传来了时断时续的歌声:“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是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 

e519d4a9-212d-440c-8982-6f5045027b3c.jpg)
189179e6-bab8-4eb6-bff2-54adb67d9acd.jpg)
aa8dcc10-d7b9-487a-9981-6ef118c4bada.jpg)
618c0fe9-533f-484d-b32b-747b2d6532b8.jpg)
2e89c7cf-37d6-43b9-8783-a3fdc2e5409d.jpg)
5cc42da7-5964-4185-b6d9-f79e919f06c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