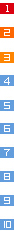延祥真的很古,开基于宋天圣太平年间,时光悠悠,一晃已过千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苏杭,只有延祥”。一个村庄繁衍生息延传百代不足为奇,一句话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且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一定有它的原因。试想,这个位于宁化、清流、明溪三县交界,有“五里横排十里岭”之称,被深山密林环绕的一个小小村落,曾几何时竟能与苏杭媲美,这要多少的底气与豪情?
千年前一个秋日,着名理学家杨时后裔杨五九途径此地,见峰峦叠嶂,青山绿水间的这块小小山间盆地,瑞鸡展翅、玉兔扑朔,顿时灵光乍现,认定是块风水宝地,乃架屋而居。而今瑞鸡玉兔不再,却留下一个让人浮想联翩富态而大气的名字-——延祥。或是以应其祥,至清代道光年间,已有灶丁4000余口,拥有山场七、八万亩,耕地四千余亩,宁、明、清三县辖地都有其土地。不仅乡民富庶,而且人才辈出。仅明、清两代有功名者就达220余人,其中进士、举人3人,职官者60人。曾获得“代有文豪”、“文豪甫着”等官府赠匾。一个村庄因为有了人文底蕴的积淀,就显得厚重了起来。
傍村的当坑溪上整天木排如林,一路直下清流嵩溪,汇闽江,达南平、抵福州。木商运出去的是木材,带回来的是一箱箱金银珠宝,同时也带回一批批能工巧匠,于是一条用青石条铺就的古街建起来了,从上村斜斜铺到下村,黛色的丛林连成一片。
有街,人烟必旺,高墙深院建起来了,亭台楼阁搭起来了。座座屋脊高翘,画栋雕梁。飞起的檐上,有着乌青的瓦当,刻着福禄寿喜财等吉祥字样。深深庭院内,书声琅琅,有长袍马褂的老先生戴着金丝镜捧着《三字经》抑扬顿挫韵味深长;镌花刻鸟窗棱后面,芝兰飘香,谁家的女子在抚琴轻弹《琵琶行》;长长地青石板道上,有马帮蹄声“嗒嗒”而过,有座轿“依依呀呀”而过。幽深的小巷,穿着绣花鞋的窈窕淑女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撑着油布伞款款走来,鞋面竟然不湿。当然也有驼着木头的汉子,汗水滴在石板上,“叭叭”直响。
这是当年的尘世繁华,如秋阳下的野菊花开,瓣瓣都是金黄的灿烂。香气一飘数百年。
历史翻过一页,再一页,千年时光,刻在了那伸向幽凉小巷的青石板路面上。我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走进延祥,昔日的风光不再,古老的石板小道上印满青苔,苍凉的青砖门楼里有墨绿的藤蔓伸出,如历史般悠长生长。我向迎面走来的汉子打听当年的私塾,他茫然望我。我扳着指头算着,正义堂、新竹第……一算竟有19所。他好奇看着我笑,反问,哪里有?
也笑,真的呢,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好多的痕迹早被雨打风吹去,何处可寻?但到底还是留了痕迹的。比如杨澹圃故居,虽然人去楼空,荒草萋萋,但照壁下那棵200多年从洛阳带回的牡丹,依然枝繁叶茂,相传曾有凤凰降此,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不得知了。只是每年鹰飞草长的时节,依旧开出粉红的花来,如约而深刻。如今这年月,守时,谈何容易,何况是年年。加上花期甚短,颇有些奔袭千里,为践一诺的味道。悄然而至,暗香浮动,牡丹算是君子。我来的不是时候,花是见不着了,见着的是一树守望家园的执着和精神。
“三五应泰公祠”如个哲人静静恭候在路旁。黛青的墙,黛青的门楼,摇摇欲坠的门楣,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匍匐于砖块上的青苔,掩盖了曾经喧嚣的岁月,用手轻轻触摸,竟是一指荒凉。当年的辉煌不再,显得一脸沧桑。沧桑自然与历史有关,没有时间的风风雨雨,又岂有沧桑可言?有风从后堂过来,从前厅过去。一只黄狗立于门楣下不作声,我亦不作声。相视无言。
青石条铺就的古街,静。黛色的高墙,每块青砖都是一页凝固的历史。两旁的门庭,那花岗岩门坎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印痕,想象得到当年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有风从小巷深处吹来,大门上锈迹深重的铜锁扣“叮当”作响,清脆。轻扣,一掌历史留下的清凉。我与谁的手印重逢了?谁又在这个门里,翘首以待,笑望月升日落?不可知了。权作一回归心似箭的男子,大门内,是否还有我朝思暮想的美人?庭院深深,有的房内还住了人,有的房内,已经不住人了。房都是上厅下廊,几进几出的,站在门外是看不出什么了,进去,好内容都在里边。
正厅都挂着古旧的匾额,有书写房堂号的,有表彰乡里的,有祝寿贺喜的,随处可寻,一眼阅尽千百年荣华。接过老妪颤微微捧上的一碗香茗,那碗沉甸甸的,图案淡雅、青亮,翻过碗底,居然是明正德年间的青花!天井里有花草长得茂盛,兰花立在瓷静盆里,绿的欣欣向荣,怕有几个世纪了。随手牵过一张椅,重实得让人惊讶。主人笑,说是上祖留下来的雕花红木椅。屋里坐着一个母亲,一顶白雪,静静望我,儿子正端着一个铜脸盆给母亲洗脸,一下一下抹着,轻得无声,若擦拭一尊珍贵的瓷器,母亲一脸灿烂如花的笑。一坐一立的两个身影,隐在一段幽暗里,是一段安详的时光,我打扰不了他们。
号称“百间房”的杨鼎铭故居是保留最为完整的一座古民居了,建于清乾隆末年(1795年),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屋宇仿照宫廷园林设计。精雕细琢,处处别具匠心。计有四坪四厅,99间房和16口天井。屋后搭花台,房前筑花圃,天井里湿漉漉的青砖上种植冬青和兰花。有斜阳从天井投下,蝙蝠翩翩飞舞。让我感兴趣的是客房里那幅对联:“师门三尺雪,相府四知金”。上联赞宋代杨时尊师好学精神,史称“程门立雪”;下联颂汉代杨震为官清廉,暮夜辞金,拒贿之美德。穿过深遂的前庭,来到后院,万字格的楼廊人去楼空,当年又是哪个美人在这妆楼了望、凭栏寄意,印下多少蹙眉凝眸、引颈顾盼的寂寞身影?美人莫凭栏,凭栏山水寒呵。
居然就遇到了村主任,在我的坚持下,从紧锁在房里,小心翼翼搬出一幅一人多高的墨绿木匾,上面题着“后昆传学业,梧冈多有凤凰毛 先代擅文名,云路已舒骐骥足”,这是清朝大书法家伊秉绶给杨氏后裔杨芳撰写的对联。村主任姓杨,是杨芳的嫡亲后裔。伊善大隶,字工四体,尤以隶书冠绝一时,与清朝另一位隶书大书法家邓石如合称“南伊北邓”。流传于世的真迹不多。今日一睹,应是前世修来的造化了。
还有宋德佑元年的古墓,南宋社坛,元末德馨祠,明、清东岳庙、崇福堂。还有明代釉花大瓷缸、清代千丝静盆、青花双喜字静盆、兰花瓷静盆、铸铜水牛、铸铁大钟、花岗石的马槽。还有清代“扬州八怪”黄慎的书画,王方元的国画。有的还留有余迹,有的已随雨打风吹去。无论岁月如何繁华,又有谁能拽住它的衣襟呢?我们能做的,一是怀念,二是珍惜。
沿了青石板道一路走去,就到当坑溪了。当年河水涟涟,木排如林,而今,水很浅了,木排是放不了了,其实也无木可放了,在这个季节里,河边的荒草和芦苇都顶一头的枯黄,夕阳的余晖打在河面上,一片金黄的颜色。一棵枫树静静立于河边,枝桠间有个硕大的鸟巢,鸟是不见了,不知去了何方。叶子开始落了,一片、一片、又一片飘到了河面上,随流水渐行渐远,像时间,一去不回头了。
我想我应该是一个怀旧的人,对有些东西总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怀,许久没有碰触的神经被我藏在内心深处,轻轻拂去历史遗留下来淡淡的一层尘和潮,思想的脉络就会变得愈加清晰。尽管时间的脚步匆匆,但人类的承接,原是错综纠缠的脉络,沿着这些脉络寻到源头,它让我们知道历史还有个名字叫厚重。它提醒我们,肩上还有一付担子叫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