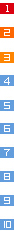1968年,母亲怀上了第五胎,怀的是我。娘舅拎着两只鸡婆和一篮鸡蛋前来探望时,跟儿子过剩粮食缺少的父母打了个赌:如果我是男的,就送他当养子。生下来后,果然是男的,体积跟小猪差不多,手指细得像筷子头。娘舅当时没敢要我,怕养不活,委托母亲把我养到2岁才移交。
小娘是娘舅惟一的孩子,小娘10岁的时候,舅母病逝。娘舅没有再娶,父女俩从此相依为命,直到我进入这个家庭。小娘原名雷赢娣,家务活样样能干样样肯干。妇女能顶半边天,小娘能顶半个娘,在我们闽北,习惯把那种特别懂事、能干的未成年少女称之为“小娘”。
在我整个童年,小小的小娘总是挺着柔弱的脊梁背着我捉泥鳅、拾田螺、摘野果、扯猪草……我伏在她的背上,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种伏在席梦思上的感觉。
5岁那年的一天黄昏,玩耍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自认为错误不在自己,而在那块该死的石头,可我又奈何不了它,于是哭着回去找小娘申冤。
小娘恰好不在家。
娘舅问我:“是不是摔倒了,自己摔的是不是?谁叫你不长眼睛,好啦,别哭了,去玩吧。”边说边伸出马路般粗糙的巴掌抺桌面似地抺去我的眼泪。
这么一来,我心里更加委屈:娘舅真不讲道理,明明是石头暗算我,却说是我自己绊倒的。
不一会,小娘打柴回来,也不管她一身臭汗,万分委屈地扑进她的怀抱,声泪俱下地控诉着我的不幸遭遇。
小娘高度重视我的不幸遭遇,立即抱着我去讨伐那块石头:“该死的石头,瞎了眼的石头,该死的,看我不踩死你踩死你踩死你……”小娘一边骂一边使劲蹬石头,直蹬得我破涕为笑为止。这时候,我反而觉得摔跤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要是那块石头小一些的话,小娘准会把扔进茅坑遗臭万年的。
依照闽北乡俗,小孩子在户外摔倒,怕丢了魂,必须“拾魂”。所以小娘在践踏完那块无辜的石头之后,又蹲下身子轮流抚摸石头和我的光头:“弟弟不怕,不怕,姐姐带你回家,弟弟不怕,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然后一路小跑把我抱回家,整个晚上都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7岁那年秋天,娘舅被抽去修水库,工地距村子有三十多里地。娘舅不常回家,平常七、八天半个月不定。节日的晚上总是要回来的。每次回来,都要想方设法带点吃的。那时候,修水库可是一项美差,因为是义务工,伙食较好,一般人还轮不上。娘舅是在给队长送了半条前门香烟才争取到名额的。工地上,吃公家的饭,队里工分照记。不光米饭,还能吃到山里人稀罕的馒头包子面条,节日还发猪肉。娘舅虽然有点家底,但平添两张嘴,很快坐吃山空,娘舅去修水库,主要是为了节省口粮。娘舅送了两斤红菇贿赂工地上的司务长,这样每次回来都能弄点好吃的给我们打牙祭。
当我们估算娘舅要回来时,心情好极了,过年似的。太阳一落山,小娘便带着我,到村头那座小山包上等待娘舅。等待过程中,小娘一边给我讲些有头无尾的故事,一边纳着鞋垫(有时缝补衣服)。乡下的女孩子,一过10岁便开始学习女红,纳鞋垫是基本功。那年小娘刚启蒙,一双鞋垫纳了一个月还没竣工,线头杂乱无章,像炸窝的蚂蚁。但是小娘进步神速,不到三年时间,一跃成村里女红高手,独领风骚十几年。
我特别爱看小娘穿针引线的姿势和神态:一根棉线,一下子就能穿入针孔,百发百中,然后拇指和无名指牵引着棉线优雅地绕一个圈,一下子就能在线的尽头处打上一个结子,然后扯直了线在雪白的米牙上砰砰两声,针尖在头发上擦抺两下,三下除五二就缝好一个扣子,从穿针到引线,整个过程中,小娘的兰花指始终翘着,像骄傲的孔雀……美不胜收。
我一边看着小娘穿针引线,一边不停催问娘舅怎么还回来。小娘不断地抬起头,说快了快了。
一天晚上,娘舅意外撞开门回来,手里用网袋拎着一个海碗,那是民工吃剩的面汤。
那天晚上,小娘就用这碗面汤给我煮面条吃。水开了,小娘左手紧握那把面,好像弹药不足的战士,一次只慎重地抽出一点下在锅里,抽了三下就不肯抽了。
中秋节的傍晚,娘舅又拎回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四个馒头,冰冷坚硬,还有一小坨肉,肥的多于瘦的,这正是我喜欢的。那时的孩子,没几个爱吃瘦肉。
小娘闩好门,涮好锅切好肉,水开了,小娘把肉小心翼翼掀进锅里。我站在灶边踮着脚眼看着锅里的水珠一个个消失,腾起一股东倒西歪的香气,我用力深呼吸,尽量不让空气占便宜。
娘舅望着我,不时用手背擦着眼睛。
吃完肉,整个晚上口里都有一股淡淡的肉味,全身上下痒痒的,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痒,不用搔,非常受用。那时我便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能吃饱肉的人。我还想,要是娘舅永远留在工地上修水库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在过年以外的日子吃上几回肉。
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冬天,娘舅真的永远留在了工地。娘舅和另外5位民工死于一场爆破引起的山体大滑坡。
娘舅这棵大树一倒,我和小娘便面临散伙的危险,许多人抢着“收养”小娘(其实是想白捡一个漂亮媳妇),至于我的归宿,当然是回到父母身边。然而,此时的我已是有家不能回,母亲已于两年前去逝,父亲脑子中风,跟傻子差不多,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自身难保,兄长们更不可能抚育我。退一万步,即使他们愿意收养我,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还不如和小娘在一起。再说,我离不开小娘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小娘也离开我。
年仅15岁的小娘毅然做出决定:她就是累死,也要把我抚养成人。
次年夏天,水稻大面积发瘟,那时治稻瘟病的特效药是石灰和六六粉,石灰和六六粉在消灭稻瘟的同时也把田里的小动物株连九族,最悲惨的要数泥鳅,尸横遍地。这个夏天是我最快乐也是最悲惨的夏天,快乐是因为捡泥鳅,悲惨是因为我的双腿被石灰和六六粉烧伤,发炎溃烂,尤其是两个腿肚子,烂得像开裂的石榴,痛得我不时发出狼一样的嚎叫,整个村庄都能听到。要不是小娘走村串户找到并请来最好的草医,我这双腿肯定保不住。我的腿每敷完一帖草药,就要像女人排月经一样排一次脓,为了减轻我的痛苦,小娘吸奶一样将我腿上恶臭扑鼻的脓水一口一口地吸出,每次都能吸出一大杯来。
现在我常想,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
三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如此一来,小娘的压力更大了,一个人忙里忙外,入春要插秧,入夏要锄草,入秋要收割,入冬要翻地,还饲养着成群结队的家畜,忙得不可开交。
我心疼小娘,表示要放弃学业回家帮她种田,平时从未动过我一根指头的小娘却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尽管小娘什么也没说,我却从她满脸的泪水读出这一掌的内涵,再也不敢吭声。
12岁那年,我考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考上高中,乡里的高中刚刚撤消,上高中必须到县城。故乡地处偏僻,距离本县反而比邻县远,我便到邻县去念高中,也不是很近,五十里,尽是山道。
报到那天,小娘起了个大早,给我煮了一碗香菇鸡蛋辣椒面。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五十山路,早出也只能晚归。我和大黄狗走在前面,小娘挑着行李走在后边,我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我知道她的心情比我还好。我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高中生,整个村庄都为我骄傲。
学校离家太远,我半月才回家一次。开始几天,我根本就无法在课堂上聚精会神,老是想念小娘,想念她的笑,想念她身上的味道,想念她穿针引线的英姿。
度日如年的半个月终于熬过去了。
星期六上午一放学,我连饭都顾不上吃,便急匆匆上路,归心似箭啊。上回说好的,小娘到半路接我。我实在害怕独自穿行那原始森林重重包围、昏暗如隧道的山路。路面铺满落叶,脚板踩在上面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恐怖极了,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不敢回头,心里一面呼唤着小娘,一面胡思乱想各种传说中的鬼怪。除了赶墟,路上极少行人,我几乎是窜着往前走。
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山顶豁口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小娘!小娘接我来了!我呐喊着冲进她怀抱,泪水浸湿了她青春的胸脯。
有一回,相隔几丈,我便闻到一股陌生而又亲切的清香。我翕动着鼻翼,小娘,你身上怎么有一股鸡蛋的味道。小娘从口袋掏出四个熟鸡蛋,递给我,狗鼻子,真灵。我相信自己的鼻子,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鸡蛋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我记不得多久没吃鸡蛋了。我接过鸡蛋,迅速剥开一个,先小咬一口,再大咬一口,最后将剩下的一半塞进嘴里,呼吸和空气都是香的,香得令人晕眩。
我剥开第二个鸡蛋,递给小娘,小娘,你也吃,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我嘴里塞着鸡蛋,语气含糊不清,说出的话却是香喷喷的。小娘推开我的手,小娘在家里吃过了,你吃,今天是吃鸡蛋的日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是小娘的生日。
为了给我壮胆,小娘想了一个好办法,每次出发时都塞给我一串花炮,感到害怕的时候,就放一颗炮。这个办法还真灵,一个学期过后,我终于锻炼出胆量,再也不用放炮,再也不用小娘接送了。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迎接和送别。
漫漫五十里山路好比天下垂下的两根绳索,结头便是高高山顶上的豁口,豁口常年穿梭着强劲的山风。豁口是个分水岭,这头连着故乡,那头连着邻县,邻县那头长,40里,故乡这头短,10里。第一个学期,回家时小娘到豁口接我,返校时又把我送到豁口。到了豁口,无论我还是小娘,先到者必然放一颗大炮给对方报信,对方听见炮响后再放一颗响应。我不知道小娘听见炮响时心情如何,反正我是热血沸腾,尤其是小娘先到达豁口时。送别时,小娘同样为我放一颗炮,祝我一路平安。这个习惯小娘一直沿袭至今,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故乡,小娘都要放一串鞭炮迎接我,走时又放一串送我,这是故乡人迎送贵客的最高礼遇。
到了高一下学期,我已经敢独自行走了,但小娘依然风雨无阻地接我送我,只是把地点转移到村头那座小山坡上。每次接我,小娘都要给自己找个理由,比如在山坡周围砍柴扯猪草或者放牛,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些野枣、草霉、山楂、山杏之类我爱吃的野果,这些都是她前一天特意为我采好的。
深秋,回校时,天气尚暖,没想到几场秋雨过后,冬天提前到来了,我正准备回家取棉衣,老天爷忽然下起了罕见的大雪,真是燕山雪花大如席呀,一下就是一个星期,积雪三尺。大雪封山,没有十天半月是不会化的,我是根本回不去了,只好裹着毯子上课。据邻居王大婶讲,最冷的那几天里,每到黄昏,小娘都要点一柱香,在家门口站一会儿,向着学校的方向远眺默默祈祷,恨不得变成一只大鸟飞越雪山给我捎去棉衣。于是,她也不穿棉衣,说是要和我一起挨冻,这样远方的我就不显得冷了。
我被小娘这种博大精深跨越时空的爱深深震撼,至今一想起就泪流满面。
转眼三年过去,我高中毕业了,没能考上大学,仅以3分之差落榜。
我当然不死心,想去补习一年,如果还考不上,那就认命,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
补习必须得到小娘的支持,小娘如果不供我,我也没办法,娘舅的那点抚恤金,早已用光。得知我还想去补习,村人都站出来为小娘打抱不平,知识越多越忘恩,文化越高越负义,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呆在故乡帮助小娘种田,她一个实在是太累了。
令人所料不及的是,小娘不仅答应了我,并且迅速把自己嫁了出去。说嫁其实不准确,小娘并没有离开故乡,而是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大我8岁的小娘这年已经27岁,姑娘家拖到这个年龄才结婚,在故乡可谓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小娘绝非嫁不出去,虽然已是27岁高龄,明里暗里喜欢她、为她睡不着觉的后生依然大有人在,其中包括村长的小儿子,以及外村一些改革开放后最先冒出来的万元户。如果不是因为我,小娘的终身大事绝不可能拖到27岁。
小娘择婿条件并不高:第一,男方必须无条件上女方家倒插门;第二,男方必须无条件支持我补习,如果考上大学,还必须毫无怨言地培养我上大学,直到我成家立业为止。
这哪里是当她的男人,简直是给我扛长工,把那些后生都吓跑了。最后一个父母双亡、家贫如洗本来要打光棍的老后生捡了这个便宜。凭心而论,我这位姐夫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老实善良,我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这当中也有他的汗马功劳,尽管他有时也给我脸色看。他没什么嗜好,就喜欢抽烟,所以每次回去,我都给他带上几条好烟。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报到那天,小娘背着小外甥坚持把我送到豁口。
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我不知道小娘在想什么,心里一片空虚。分手时,她站到我面前,我这才发现她哭了,眼睛都哭肿了。
小娘很激动,张口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从背着小外甥的背带里取出一个小布包塞给我,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两千响的鞭炮点燃扔在我脚下,然后双肩猛地一抖,扭身发疯似地哭着跑了,背上的外甥吓得哭了起来。
望着小娘消逝的身影,我再也控制不住,泪如雨下,朝着相反的方向奋命跑去……
也不知跑了多远,直到跑不动了,我才坐在地上,打开布包一看,是200元钱和6双构图新颖巧夺天工的鞋垫,有方格套的,有环套的,有莲花的,菊花的,梅花的。
这6双鞋垫我一直精心收藏着,那上面密密麻麻地缝着小娘对我无尽的爱。若干年后,我从村人口中得知:成为养父的养子不久,我就和小娘换了帖子,也就是说,我和小娘订了娃娃亲。当我得知这个秘密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愧疚无比的我真想跪在她面前,惊天动地地叫一声“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