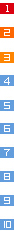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


血经副本,字迹鲜红

胡善美向记者讲述血经转运一事
(记者 吴剑杰 见习记者 吴建萍 林良划 文/图)
2015年5月中旬的一天,福州鼓山涌泉寺81岁的正茂法师向东南快报记者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铁箱子”的日子,显得十分吃力,他是涌泉寺年纪最大的法师,也是寺内跟那段兵荒马乱的岁月最接近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当局让沿海各地重要文物,向内地山区迁移保藏。1939年,涌泉寺当时的住持圆瑛法师立即组织力量将寺内最珍贵的20箱经文转运到尤溪县。福州沦陷后,日寇果真到了寺内,但终究扑了空,那时的正茂法师还没入寺,日后看到装经书的铁箱子,已是六十年代了。
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民间与涌泉寺在佛教文化上便有过交集,涌泉寺部分经书经日本学者调查研究后,拍照带回日本,并影印流传开来。日后,涌泉寺还是遭到日本侵略者觊觎,但对于转运的经文,僧侣们始终缄口不言。
而抗战之时,圆瑛法师组织僧侣救护队,甚至带徒弟下南洋筹募善款,支援前线。寺内的僧侣也积极参与省会青年组织抗战。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从知情人的零星记忆里,梳理出部分文献资料,试图揭开那段转移经文的历史,以及属于这座古老寺庙的抗战史。
运送经书的铁箱焊接密封而成,六十年代还曾存在
谈到五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正茂法师兴致颇高。“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多”,寺内的僧人告诉东南快报记者。
见到废旧的铁皮箱子时,具体年份应该在1963-1964年,“箱子是用铁皮焊接上的,纯黑色”,正茂法师说,“铁箱子大概有半米多高”,呈长方体结构,正茂法师向记者比划着,不过看到它时,铁皮箱子已经破旧不堪,如果不是老师傅提及,当时才二十多岁的他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废物”。
“那就是当年运到尤溪用来装经书的箱子”,老师傅告诉他,数量大概有十几个,经书早已上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茂法师连铁皮箱子也见不到了,“估计被人当废铁拿去卖了”。
正茂法师1963年进涌泉寺,时常从老师傅的闲谈中得知当时经书转移的事情,但零零散散,支离破碎,他只记得,老师傅们简单地谈到当时如何将经书包装入内,然后让和尚将经书挑到船上,最后再溯江而上,深入尤溪内地,进行保藏。
寺内和尚建议运往尤溪寺庙保藏,对于所运经书和尚缄口不言
1955年,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大一学生胡善美,因为帮当时的部队测绘鼓山地图,全班三十多人有幸在涌泉寺住了二十多天。
胡善美从当时寺内一位四五十岁的和尚口中了解到关于经书转运的部分细节,“当时寺内忌惮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和尚可能被杀,庙可能被烧,但经书要是被毁或是被抢走,那麻烦就大了”,胡善美的老师告诉学生,一个寺庙是否闻名,最终要看的是寺庙所藏佛经的数量和质量。
因为与老和尚熟识,胡善美有幸进入当时储藏经书的房间内看过,“满满当当的,几大壁橱,上面写有康熙乾隆字样,这里面的经书不让看”,他说,老和尚回忆,当时寺内打算把经书转移出去,但对于转移的地点有过争论。
南洋?也被日军占领;英法?路途遥远,终归不安全。“想来想去,最终还得靠自己转到闽北地区”。但具体藏在闽北的哪个地方,也尚未有定论,胡善美说,那时寺内刚好有一个尤溪的和尚,出面建议可以往尤溪内陆移藏,他对尤溪的寺庙比较了解,知道哪个寺庙藏佛经比较安全,为此,该和尚还多次回尤溪踩点,并安排相关事宜。
涌泉寺有近万册经书,不可能全部转运,一个是目标过大,另外一个时间紧迫。胡善美说,寺内重点挑选了部分经书。老和尚回忆,挑选的经书被僧侣们从山上挑到闽江口。“载经书的船是那种小渔舟,顶上弓着一张帐篷”,寺内的和尚都被教诲,切不可将经书转移一事泄露出去,对于铁箱子内所装的经书,正茂法师并不是非常了解,只记得有“血经”及其他珍贵经文在内。胡善美也感到好奇,但当时老和尚对此事缄口不言,学生们也不敢继续追问。

圆瑛法师(资料图)

涌泉寺珍贵经文清代龙藏

储藏皇帝钦颁的经文的橱柜
铁箱内藏有血经,系高僧用鲜血配金粉写就
福州开元寺方丈、圆瑛法师的徒孙本性法师告诉东南快报记者,当时由圆瑛法师亲自护送的20箱经文,其中就包括元代的《延祐藏》。据了解,至民国期间,《延祐藏》全国只有鼓山涌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有保存。
除此之外,还有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两代刺血写的佛经以及国内罕见的珍贵版本。涌泉寺始建于783年,1407年改称涌泉寺。其中不乏康熙和乾隆皇帝钦赐入寺供奉的经书,甚至还有来自印度和缅甸的贝叶经,以及9部657册刺血写的经书。
在涌泉寺藏经殿的大厅内,玻璃橱窗里摆着上述部分珍贵经文的副本,也有清代高僧的血经,文字清晰可见,颜色鲜红。
在涌泉寺藏经阁内看殿的智和法师告诉记者,用血写成的经书,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及大量的鲜血,“供血的高僧,要长期不吃盐,血液就不会凝固”,胡善美说,“鲜血配以金粉,色泽金红,为防止虫蛀,还得加以适量的明矾”。
经书走水路到尤溪再转运,雇百名挑夫秘藏三峰寺
这些珍贵经书如何走水路顺利运抵尤溪的三峰寺,这些经历,涌泉寺几乎没有多少相关记载。
三明尤溪县政协文史学习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张玉红主任也有此类困惑,而据张玉红查找尤溪文史资料得知,在一篇由时任尤溪县长的童庆鸣口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的《鼓山涌泉寺<大乘经>版运抵尤溪三峰寺的经过》的文章中,部分疑问似乎得到了解答。
童庆鸣回忆,日寇进逼东南各省,“为保护鼓山涌泉寺储藏的国内外稀世之宝《大乘经》版,防止落入日军之手”,省府密电尤溪县政府,要将其运抵尤溪保藏,他立即委托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詹宣猷办理此事,由詹宣猷准备秘藏地点和搬运事宜。
1939年7月,圆瑛法师亲自护送的二十箱经书用轮船秘密运到尤溪口,然后再由木船运载到尤溪县城,之后又动用了百来人秘密挑往位于纪洪乡的三峰寺(现在位于管前乡,“文革”中被毁)。
对于为何选择在这座寺庙,张玉红说,文中只有寥寥数语带过,“该寺建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清康熙22年重修,乾隆八年僧端本增茸,高筑在群山之巅,风景幽美,气候凉爽,有众僧住寺”,而这些经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新运回涌泉寺,“但据1957年清点,原有762卷的《延祐藏》仅存600多卷,损失的大多是补抄的50卷”,本性法师说。
福州沦陷时,日本军官曾到涌泉寺询问佛经去向
这提前的转移,事后被证明完全正确。胡善美告诉东南快报记者,福州沦陷期间,曾有日本军官带着两个卫兵闯入涌泉寺,自称是研究佛经的“学者”,谈吐谦谦有礼,并要求参观寺藏佛经,守寺和尚无奈之下打开藏经殿,这名日本军官翻了两个多小时后并不满意,又追问寺僧,是否有其他佛经藏在别的地方,寺僧并未透露出转移经文的去向,只是答,“没有了,都在这里”。
事实上,日本人与涌泉寺佛经的渊源远不止于此,日后是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的胡善美曾对与涌泉寺相关的书籍资料有过收集,并经过一番考究,1929年(日本昭和四年)春,日本常盘大定博士携人到中国进行“南中国佛教史迹调查”,至鼓山涌泉寺查看后,“至少有四五十部佛教经典著作他们没有”,后称涌泉寺为“中国的第一法窟”。
胡善美曾在文章里提到,在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杨树庄的帮助下,常盘大定全面核对了涌泉寺和长庆寺藏经的目录,还把日本所没有的有关佛典,逐册逐页拍照带回日本,影印流通。并且写了《支那佛教史迹纪念集评解》一书,在东京印行。
而与弘一法师私交甚好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也曾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被弘一法师认为藏在涌泉寺“或为吾国现存之最古之经版”的康熙时版的《华严经疏论纂要》,由苏慧纯居士印了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给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送到尊处(内山完造)。”据文献显示,《华严经疏论纂要》,就是清初鼓山涌泉寺住持道霈(1614-1702年)禅师所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这是其耗费十年光阴在唐朝佛教名著《华严疏钞》、《华严经论》的基础上,重新删节订正而成的中国佛学经典代表性著作之一,共120卷,分装48册,是仍未收入藏经的巨著。
以上可见当时日本民间与涌泉寺早已有所往来,并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圆瑛法师曾组织僧侣救护队支援抗战,并下南洋筹募善款
日后,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几近中断,涌泉寺住持圆瑛法师在苏沪积极组织僧侣救护队支援抗战。
本性法师告诉记者,早在民国廿六年(1937年),圆瑛法师就组织召集苏沪佛教界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等待战时之用,经训练月余,“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
僧侣救护队就用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和伤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一时间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直到上海沦陷之后,僧侣救护队随军由沪沿途至南京,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但当时战时纷乱,各处收容所经费甚紧,十月间,圆瑛法师亲自前往南洋马来亚半岛,募集医药费,以资接济。随后圆瑛法师与徒弟明旸法师一起前往新加坡等地筹募善款,组织第二第三僧侣救护队,皆得偿所愿。
但在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但他们始终毫无畏惧,经多方营救,才最终脱险。因为忙于抗战,圆瑛法师甚至无暇打理涌泉寺。东南快报记者在福建省档案馆内,查询到一份于1946年5月份呈交,名为《鼓山涌泉寺寺产被敌抢掠请求救济》的资料档案,当时的鼓山涌泉寺住持虚云法师向国民政府申请救济,内文写道,涌泉寺因日寇两度入侵福州而鼓山首当其冲,“僧等本国民之责即前住持圆瑛和尚奔走南洋群岛募集巨款,创办僧侣救护团并设难民收容所于战地之后方收容战区难胞,故对本山僧众生活以及物资生产不能兼顾”。
虚云法师述及,青年僧侣只得以劳力开垦耕作,来维持生活,沦陷期间也参加省会有志青年支持抗战,但因敌人劫掠生产物资及财物,致使众僧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即便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善美回忆当初在寺庙内与众僧一同生活时的情景,也觉得寺内艰苦,僧侣很清贫,自己饭也不敢多吃。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涌泉寺时常有一些日本游客前来参观,照看藏经殿的智和法师对此仍然小有警惕,通往鼓山的道路也比以前更为通达。这个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的古庙,在民族危难之时,不惜介入到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即便寺庙曾被敌两次劫掠,“更以威胁行动之自由”,但僧侣们依然坚持民族大义,正如虚云法师对威胁所做出的回应,“僧本佛陀无畏之精神终不屈服,艰苦响义以期国家与宗教共存亡,矢志不敢稍逾移”。
圆瑛法师年谱
圆瑛(1878-1953年)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先后师从各禅宗名师,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等,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
圆瑛法师也是位爱国的高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界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战场,救护伤员。还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携徒明旸法师到新加坡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根据明旸法师主编的《圆瑛法师年谱》等相关著作综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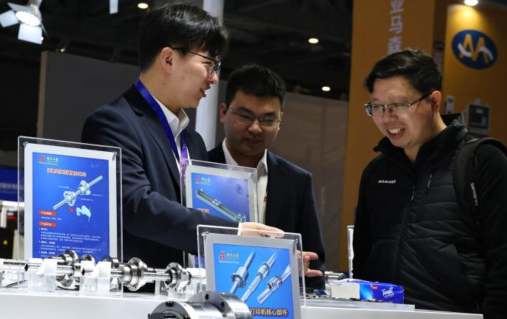
6a021623-d855-40a7-9bf8-08aaf5b66ab0.jpg)
a5de7127-e69e-478c-81e7-3e61224028e2.jpg)


6d31388c-2019-4d9d-adcf-8fd48284b2ea.jpg)